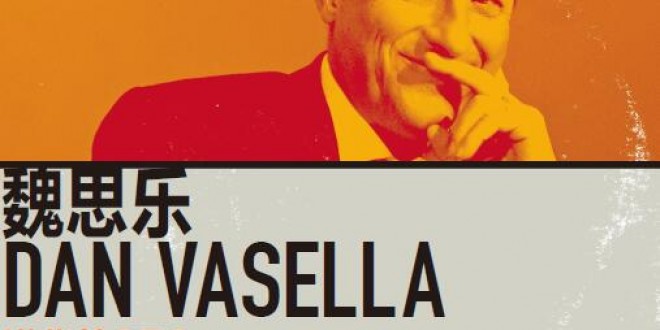当组织陷入困境,解决的办法通常是修复文化。几乎人人都说,通用汽车在2014年遭遇汽车召回危机后,需要做的事就是修复文化。而自召回事件以后,通用CEO玛丽·芭拉(Mary Barra)就一直致力于创造“正确的环境”,来增强责任感,避免再次发生危机。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the U.S.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简称VA)曾拖延退伍军人接受必要治疗的等待时间达数月之久,因此被联邦调查员指称体制腐败。事件曝光后,专家到处呼吁通过修复文化解决问题。同样,文化变革也被提议作为防止警察部门过度使用武力、银行不道德行为和任何你能想到的重大组织问题的解决方案。所有人都将文化视为问题的原因和对策。
但我们采访的企业领导者——曾成功领导重要变革的现任和前任CEO称,文化不是让你修复的东西。在他们的经验中,文化变革应是实行新流程或结构(比如修改过时的战略或商业模式)应对业务挑战后得到的成果。你在做实事的同时,文化就演进了。
尽管我们采访的CEO对文化的认识,与通用汽车和VA等组织扭转危机所用的理念有冲突,但将文化视为结果,而非原因或解决方案,在直觉上是成立的。组织是会产生连锁反应的复杂系统,修改基础流程必然将带来新的价值观和行为。员工会开始从全新的角度看待自己对社会的贡献,比如艺康公司(Ecolab)CEO道格·贝克(Doug Baker)为加强客户关系,将权力下放到前线的过程中,就改变了员工的视角。或者,员工对高管的敌对情绪也可能得到缓解,例如达美航空(Delta)CEO理查德·安德森(Richard Anderson)在收购西北航空后,通过满足原西北航空员工的正当需求,赢得支持。
我们采访的领导者目标不同,采取的做法也不同。比如艾伦·穆拉利(Alan Mulally)致力于消除福特各部门之间的隔阂,而魏思乐(Daniel Vasella)下了很大功夫将权力下放,解放诺华的创造力。但在所有例子中,每当领导者使用工具(如决策权利、绩效考核和奖励制度)解决自己所面临的业务挑战时,组织文化都会以奇妙的方式随之演进,进一步确定新方向。
回顾这些领导者的故事,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到企业变革以及文化在变革中的作用,于是我们分享了访谈中最精彩的部分。多数故事涉及并购整合方面的事务——这是企业最难实现的过渡之一。所有故事都表明,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不是终点,它随公司的竞争环境和目标而改变。文化更像是暂时的停驻点——如果应对挑战的方法正确,文化就是组织当下应该在的位置。
道格·贝克
道格·贝克于2004年接任工业清洗剂制造商艺康CEO。当时公司收入是40亿美元,贝克大胆地把目标定为收入翻两倍。到2014年,他完成了大约50次收购,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收购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内珀维尔市的水处理公司纳尔科(Nalco)。艺康销售额增长到140亿美元,员工数量增加了一倍多。
艺康通过收购,有能力提供更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特别是一站式购物),满足客户的清洁需要。但每当艺康兼并一个新实体,复杂性就会增加。组织层级成倍增加,管理者被分派到不同的办公室和部门中。主要决策者与客户和其他决策者交流的时间减少。官僚作风不断加重,腐蚀了艺康以客户为中心的文化,导致业务受损。
贝克想重新回归艺康的核心竞争力:客户至上。艺康的模式是,让客户亲自到公司来参加评估和培训,以此为基础,为每位客户打造个性化的产品及服务组合。很多客户都和艺康合作多年,与他们保持稳固关系至关重要。
贝克认为,问题的答案是精心培训与客户接触最密切的一线员工,鼓励他们自主做决定。他们对公司所提供产品和服务了解越多,就越有能力自主决定什么解决方案可以满足客户的需要。
将决策权下放似乎有风险,但贝克发现,用这种方法能更快地找到并修改不明智的决定。最终,管理者开始放权并信任员工——这是个巨大的文化改变。培训员工需要时间,而且还要随客户偏好和业务动态的变化,不断调整培训方案并重新评估。但最终,艺康通过培养一线员工责任感,维护了客户关系。
贝克还强调了任人唯贤的管理方式对激励员工完成企业目标的重要性。他说:“员工会留意谁得到晋升。”升职等奖励被用来表彰公司珍视的行为类型。久而久之,贝克发现,公开表扬甚至比财务激励更重要。他指出:“你召集员工来做什么?你赞扬什么?员工如何获得同辈赏识?奖金不是不重要,但是不会让大家知道。”好的管理者,会将决策权交给与客户面对面接触的员工,并且在员工表现积极时鼓励员工发挥带头作用。
在艺康收购的小公司中,下放决策权尤为重要。很多被艺康收购的私企都使用“家长制”(father knows best)管理员工:创始人发出命令,员工照办。虽然“家长制”在小型组织中行得通,但会阻碍艺康的发展,加大跨部门合作难度。
随着前线员工因维护客户关系和相互协作而受到奖励,一种自主的文化开始形成了。管理层也得以腾出时间关注更宏观的问题。若各级员工都感到自己受到信任,反过来也会更相信公司,并开始视其工作和使命(让世界更干净、安全和健康)为对社会的真正贡献。员工在对自己工作的看法得到升华后,就能看到自己正在让客户的生活更美好。但员工思维模式的转变需要时间,因为每次收购后,都要再进行一次转变。
“被收购企业的员工不会立刻就爱上新公司。”贝克说,“爱需要时间。”
理查德·安德森
理查德·安德森刚就任达美CEO不久,就领导了达美在2008年对西北航空的收购。完成收购后,达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大概有7万名员工。当时两家航空公司都正在走出破产保护的阴影,进入航空旅行的严重低迷时期。
安德森没有像贝克一样,在并购后循序渐进地进行整合。他觉得,收购要快速而强势,他没有时间和意愿赢得员工的喜爱。“不存在平等合并这种事,”他说,“在这儿,一切都由我们做主。公司总部将设在亚特兰大,名字将是达美,而且不会有联合品牌。我们收购的方式相当霸道。”
要在极其复杂的行业中快速整合不同系统、流程和人员,安德森必须给周围的人领导权。他坚信,公司应有一个没有决策权的主席,负责监管董事会日程和流程,还要有一个独立处理业务的总裁。“总裁和我有同等的威信,”安德森说,“所以我们的工作量是一个领导者的两倍。我在中国跟两个合作伙伴谈协议的时候,他可以负责收购维珍亚特兰大航空(Virgin Atlantic)的股份。”安德森还让他的首席运营官和首席营销官分担了很多责任。
安德森曾任西北航空CEO达3年半之久,所以对这家公司的了解比较透彻——他清楚自己将在西北航空遇到一个大障碍。西北航空工会化程度极高,在安德森看来,这会让员工和管理层之间处于对抗状态,造成双方沟通困难。管理层依靠工会了解员工需要,却不直接与员工交流。由于管理层和员工都依靠第三方进行交流,双方解决问题的时间就延长了。
所以,进行快速整合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与员工建立稳固关系(在安德森明确达美是控制局面的一方之后)。于是安德森开始设法满足员工需要并激励他们为公司和客户认真服务。他决定着重满足员工的工作和个人需要。达美为员工提供一流的培训、弹性工作时间、设备先进且维护良好的飞机,以及舒适的员工酒店。这些福利成本并不高,特别是与航空燃料相比,但在员工忠诚度和信任度方面得到的回报很是可观。
付给员工足够多的报酬也很重要——高酬劳可以激励员工积极表现。“你希望员工工作效率高,努力,而且把所有事都做好,”安德森说,“但作为回报,你要提供相当完善的福利体系和薪酬体系。”达美每年都在缴税和发放管理层薪水前,将收入的10%用于发放员工奖金。兼并西北航空一年后,达美将公司股权的15%用于员工(包括飞行员、空服人员、地勤和支持人员)持股计划。薪酬上涨,表现出管理层对员工的关爱,有利于进一步构建相互信任的文化。
安德森还认识到,每个员工都有特别的需要。以值早班的设备维修工人为例。“今天早上明尼阿波利斯市室外温度是零下10度,还有暴风雪,但他们还是要把工作做完,”安德森说,“他们要在一堆除冰桶中站起身,给飞机除冰,然后离开登机口。”
安德森在满足员工需要上作出的努力似乎彻底改变了员工与管理层之间令人不安的敌对状态。在他担任CEO两年后,达美员工投票决定撤销工会(但飞行员除外,因为他们通过工会与其他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比较,从而获得行业影响)。如今,除中东的航空公司外,达美是惟一多数员工都未加入工会的大型航空公司。
员工越幸福,就越愿意留下。于是达美的“终生员工”文化越来越盛行,而安德森视之为好事。“我们公司有很多40到45岁的员工,而且他们可能是第二或第三代员工,”他说,“但公司不存在裙带关系的潜规则,因为我希望同一家族的数代人都在达美工作。”他的理念是,让员工的亲戚加入达美往往能提高整体忠诚度。有关系的新雇员进入达美时就对公司有一定了解,而且对公司运营方式的看法是正面的。
艾伦·穆拉利
艾伦·穆拉利于2006年执掌福特时,公司正处在破产边缘,而且自1990年以来,已经失去了将近25%的市场份额。但穆拉利曾领导波音公司走出低谷,他知道如何在危机中作出艰难决定并果断执行。他第一次在福特开财务会时意识到,再过几个月,公司资金就耗尽了。但穆拉利扭转了公司的破产轨道:在他2014年离开之前,福特连续5年实现盈利,股价也大幅上涨。
然而穆拉利面临的挑战不只是财务方面的。要将福特拉回正轨,他必须加强管理层成员之间的协作。福特管理层是出了名的残酷冷血而且富有攻击性。不同部门的高管互相隐瞒信息,而非大方分享。穆拉利说,当他接管福特时,该公司就像“一堆独立的公司”拼凑在一起。每个部门制造的汽车都不同,针对的市场也不同,而且运营是完全独立的——这些因素都强化了“各自为营”的防卫心态,并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穆拉利根据自己在波音的经验,要求几个不同级别的高管定期开会,分享各自部门的最新情况。这些高管用彩色编码系统(color-coded system,绿色代表很好,黄色代表要注意,红色代表出问题了)快速并全面地评估福特在多个项目中的整体表现。
在公司问题最多的时候,高管小组每天都开会。穆拉利希望会议能帮助高管在问题变得棘手前就发现苗头,他鼓励高管分享想法并彼此提供支持。穆拉利还希望培养个人责任感;管理者必须说明自己遇到的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进展。
穆拉利还制定了“一个福特”(One Ford)战略,旨在通过整合福特在世界各地的部门,减少浪费并精简流程。他设立了生产、营销和产品开发全球主管的职位,负责领导全球协作和简化运营。
当所有高管都进行团队协作且保持信息公开时,穆拉利可以轻易发现表现不佳的品牌。他卖掉了几个福特豪华汽车品牌,以便集中生产有发展潜力的小型节能汽车,包括嘉年华(Fiesta)和福克斯(Focus)。福特回归了最初的使命:为大众生产高质量汽车。
在变革开始时,高管们害怕提出问题,担心同事会揪出自己的弱点。最初几次会议中,所有表格都是绿的,但穆拉利把表格推了回去,说:“我们过去一年失去了数十亿美元,而你们现在告诉我公司没问题?”最终,几个勇敢的高管(其中一人是马克·菲尔兹(Mark Fields),后来接替穆拉利成为福特CEO)开始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而穆拉利赞扬了他们的坦率。最后,所有高管都发现,坦诚让他们能够一起共事并快速找到解决方案,他们的表格也反映出所在部门的真实情况。
魏思乐
魏思乐在1996年策划了山德士(Sandoz)与汽巴-嘉基(Ciba-Geigy)的合并后,被任命为合并后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家新公司就是诺华,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药企业。
为满足更多种客户需要并更好地隔离公司,魏思乐带领公司转型,产品从单一的处方药转为多种保健品。这一重大变革要求组织变得更复杂。
对魏思乐而言,领导变革从培养最高层的目标感开始。他和一小部分高管在一系列初期讨论中确定了公司的愿景和目标。首要目标——“发现、发展和不断给患者带来更好的药品”就是直接针对拓展公司产品种类的挑战。为实现这一目标,魏思乐在任职期间加大了研发投入。
魏思乐还在会议中阐明对员工的期望。首先,员工头脑要灵活。随着新药品的开发,没人能够预料到诺华将面临怎样的挑战,所以团队必须灵活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此外,员工必须有责任感并把客户的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为改变员工思维模式,魏思乐在公司日益多元化的部门和产品小组中,设立了明确的绩效评估和质量保障指标。随着诺华的发展,他知道更多人需要负起管理的责任,而一个良好的绩效管理系统能帮助员工把精力放在正确的事情上。“你还必须说明你不能容忍什么,”他说,“我不容忍贿赂,不会纵容公司内部的不正之风。”
魏思乐认为,不应强迫一家还处在上升期的公司实现部门之间的协作和联合,于是他将决策权下放,给员工权力去做对所在部门最有利的事情。他觉得,权力下放使团队动作更快捷,想法和行动也更具创意。
“我的观点是,关注外界——关注竞争和客户,”他说,“如果你无须与他人开展合作,就别因为担心有没有表现出协作精神,束缚住自己或放缓行动。”
诺华实行新措施后,员工更注重客户和业绩。“开始你必须给客户想要的(更有效的药品和疫苗),”魏思乐说,“接下来就可以为付出索取回报。”他每次对组织进行变革,都意识到公司文化正向他和高管在早期会议上制定的变革纲领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