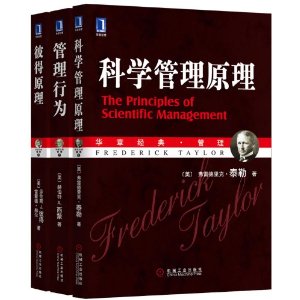泰勒认为管理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使雇主的财富最大化,同时也使每一位雇员的财富最大化”。他的目标定位很直接也很实在,不拖泥带水,也不浪漫主义。这一点就像他后来创立的“科学管理”,其理论建立在现实主义、实证主义经验论上,认为资方和劳方根本是两个冲突的利益群体,其背后的价值立场也必然对立冲突,因此不存在什么美好的和谐共处,除非能做到在保持雇主低产品工时成本的同时确保工人的高薪需求。然而,问题是这对矛盾能被消除,化为统一吗?泰勒自信可以,而且只有“在科学管理下,将会更富裕、更快乐、不协调和纠纷将更少;而不景气的时期会更少些、更短些,所遭痛苦也更小些”。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泰勒的“科学管理”着实简单。它无非说的是:通过弄清楚一个劳工一天应有的产量或作业量,确定一个劳工的日标准作业量,使劳资双方都相信这是一个“客观公正”的基准。有了科学研究确定的“日标准作业量”后,就可以参照劳动力价格的行业水平,确定“工资支付率”,即确定每件产品的工资金额。于是,剩下的事情就是逐渐把管理行为纳入到劳工群体的生产作业过程中,以及建立基于“差别计件工资制”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即激励和约束劳工群体为企业的整体目标努力工作,提高效率。泰勒的这个思想用现在的话来说,指的其实就是类似“社会无差别劳动”的定价基准(里面包含了人力成本、生产成本等)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激励机制。看似简单,也几乎成为了一种常识,但是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以上生产管理理念,却是非洞见、前瞻所不能做到的。在这个意义上,泰勒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第一位认真研究劳动的人”,“第一位把管理当作一门学科的人”,受之无愧,实至名归。
不过,历史总爱给人开玩笑,不管是善意还是恶意。泰勒坚信其“科学管理”能让企业管理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得到彻底而系统地解决。可是在1911年,曾在两年前引入泰勒管理制度的波士顿沃特敦兵工厂引发了大罢工;1912年,美国国会迫于压力组成特别委员会,举行听证;1913年,国会特别委员会向美国上下两议院提出“禁止泰勒制”的法律提案;1915年,两院通过了这项法案;期间芝加哥大学霍克斯(Robert F. Hoxie)教授发表了《霍可斯报告》,结论是泰勒制的本质是一种无视劳工人格,不断提高劳动强度的制度体系,并且,对一流的熟练劳工的工作方法、知识与技能进行提炼,形成标准的作业方法与作业量,消除了熟练劳工与非熟练劳工之间的差别,使所有劳工如同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一样,统一于生产作业过程之中。但有意思的是,美国总工会不久又承认了泰勒制,承认科学管理对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工业社会发展的价值。与此同时,强调任何企业在引入科学管理之时,都必须就有关劳工的工作条件与待遇等问题,与工会团体进行协商,达成劳资间的协议,避免给劳动者带来不利影响。
而到了二十一世纪,当“现代组织理论”深入人心,泰勒的“科学管理”已日益暴露出弊端。最主要的是,泰勒认为能找到劳资两利的结合点,消除劳资对立的方法实际上作用有限。按照现代组织理论,正确解决企业内部的利益对立关系的办法是,依靠使命愿景和战略目标来统一组织成员的价值立场,依靠源于价值立场的制度性规范来统一各自对立的利益关系。也只有在这个框架内,才能更大限度地发挥组织内的协同效应,进入更广阔的价值创造空间。而泰勒的“科学管理”更只是局限在利益提成、绩效工资层面上,属于一种激励机制,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资对立问题。同时,泰勒希望依靠科学研究的方法确定“标准作业量”,然后确定“工资支付率”,这在理论上是很完美的,但在实践上却是行不通的。尽管科学研究可以确定单位时间的作业量,但最终还是不能依据作业量来确定工资多少,毕竟前者是事实评估,后者是(劳动力)价值评估,两者不可直接划等号。
当然,泰勒的“科学管理”在现代管理也并非一无是处。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泰勒的建议是相当可行的。具体应用到管理的实践,泰勒给我们的启发是,要重视对员工的激励,以一种劳资双方都认可的生产标准为基准,确定奖励方案(物质的或精神层面的),最大限度调动员工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提高组织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