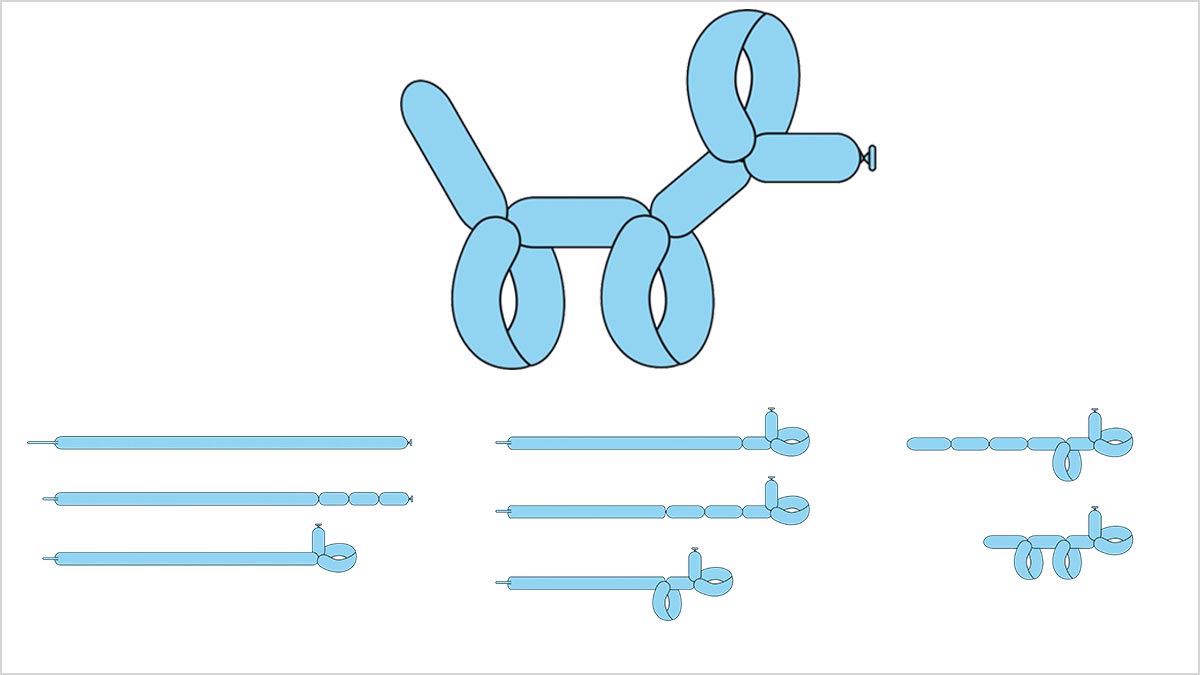欧盟已经花了20年的时间试图创造一些市场条件,以便创造出数字经济中和其他地方的那种爆炸式增长。到目前为止,前述的努力都没有奏效。所有能做的努力,欧洲几乎都已经尝试过了,最近期的是欧盟执委会主席当选人尚克劳德•荣克(Jean-Claude Juncker)所提出的新架构。
在今天最大的15家上市互联网企业中,没有一家来自欧洲。十一家总部在美国,其余的都是中国企业。
这个问题经常简化为一个问题:欧洲如何创建自己的硅谷?
自从网际网络革命以来,我就一直在北加州定居及工作,无论是在国内或国外,我常被问到上述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通过适宜的法律。
当然,加州之所以能独领风骚,硅谷生活的某些突出特点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些特点,有一些是精心设计的,有的纯属巧合。最重要的,是两所主要的研究型大学,加州大学柏克利校区和斯坦福大学,它们是硅谷的职业学校。而说到吸引更多人才到该地区,北加州的天气和优美的景色绝对是优势。然后就是1960年代电脑和反主流文化的意外交流。正如约翰•马可夫(John Markoff)在他2005年出版的《PC迷幻纪事》(What the Dormouse Said)当中指出,苹果(Apple)和微软(Microsoft)这些电脑公司的使命和性格,都源自于嬉皮生活方式和迅速改善的半导体性能与价格,这两件事意外地混合交织在一起;而半导体性能和价格之所以能迅速改善,是根据一项后来闻名全球的当地法则“摩尔定律”(Moore’s Law)。个人的成长,原来是需要靠个人电脑。
不过,在欧洲也有很多一流的大学,欧洲的生活品质很难以超越,而且不乏许多哲学想法能提高人们对很多议题的重视。政府和私人投资者已经建立了创业育成机构,主办“骇客松”活动,并付出大量的种子资金。那么,为什么欧洲仍一再失去创建硅谷的机会?
硅谷,其实是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建设上的。第一个是实体的,集中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和研究园区,以及从斯坦福大学棕榈大道(Palm Drive)向外扩散的Google、苹果、脸书等闪亮新兴的公司所组成的企业社区。
而第二项基础建设,则是与第一项同样重要的一套法规架构,其中包含了数十年来采行的法律和政策,甚至连硅谷的居民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这些规则极少是为了电脑或甚至科技而制定的。但所有这些法规共同引导了硅谷的发展方向,影响力高于硅谷重镇帕罗奥图市(Palo Alto)大学大道两旁所有中、高档餐厅午餐聚会里做成的所有决定。
我在这里先提出四个对加州科技产业格外重要的法规,这些都是与人力资本或金融资本有的的法规:
非竞争条款——加州是世界上唯一断然拒绝执行非竞争条款的司法管辖范围,此条款被编入《加州商业及专业守则》(Business and Professions Code)第16600条。雇主不能依法阻止员工加入竞争的公司,即使短暂地阻止都不行。该法律的源起可追溯到1872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这条法律让工程和创业人才能在硅谷内不断流动。新创企业可以聘请他们需要的明星人才;而既有的公司必须致力加强创造让人才觉得值得的工作环境,以吸引和留住人才。他们都不需要工会。
就业的意愿——反过来看,在加州就业被认为理所当然是“随意”的。雇用和解雇对双方来讲,都是一个相对简单的过程(明确的例外情况是年龄、种族及性别歧视)。随着新的企业扩大规模,他们可以很有效率地快速增加人手。如果新创企业失败或变得与原先规划很不一样(这些情况经常发生),缩减规模也一样地容易。在硅谷变换工作频繁,创意及人力的交换往往通过创投公司做中介。
谨慎人规则(The Prudent Man Rule)——1978年间,美国劳工部放松了对机构投资人的一大限制,也就是被称为“谨慎人规则”的规定,这项规定禁止退休基金和其他信托基金参与高风险的活动。其结果是大量资金流入,包括从加州州政府公务员的退休基金CalPERS等机构。这彻底改变了创业投资活动,并创造了硅谷庞大的创投引擎。创投公司提供资金,促成了这个区域内、外每一个重要的创新。并且效果很快显现。私人投资者运作的速度像闪电般迅速,完全不同于政府提供资金的单位。
差别资本利得率——资本利得与普通收入的税率,通常被认为是对创投资本流动最重要的影响因素。联邦税法在1978到1981年间,将这种收益的税率从49%降到20%。不同的税率有助于抵消创业投资的较高风险,迎来大量的资金投入新科技的新时代。根据美国国家创业投资协会的数据显示,单是2014年就高达480亿美元。放宽“谨慎人规则”,让机构投资人得以参与;降低税率则进一步吸引他们参与。
我所列出的项目并未涵盖所有因素。威廉•拜格雷(William D. Bygrave)和杰夫•提孟斯(Jeffry A. Timmons)1992年出版了一本书《创投面临十字路口》 (Venture Capital at the Crossroads),书中介绍了其他几项政策优势,包括简化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对股票发行和店头市场(例如纳斯达克[NASDAQ])的程序;以合乎效率的成本来保护劳工与环境的基本法令;平衡知识产权和反托拉斯法;以及政府资助基础科学研究,其中大部分,是在冷战期间来自美国国防部的资金,这在加州已有悠久的历史。
特别是针对网际网络革命,我们还应该加上柯林顿政府时期所采用有远见的两党政策,让网络经济(包括硬件、软件和网络基础建设)大部分都不受法规管制,也不必纳税,也就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马凯特斯中心(Mercatus Center)的亚当·希勒雅(Adam Thierer)所谓的“无须许可的创新”(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
欧盟,就如新的数字单一市场的提案所指出,终于看到了这项政策的智慧(讽刺的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正威胁要撤销这项政策)。欧盟也看出本身需要一个顺畅的“无摩擦市场”,好让资讯产品和服务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美国消费者认为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另一项柯林顿时代留下来的智慧,是美国的一条法律,称为Section 230。它是1996年通讯传播法案的一部分,让网络公司、网站主机和网络服务供应商,不必承担使用者所发布内容的法律责任。很难想像,若是没有这个法规,如何能够发生脸书、推特(Twitter)、Instagram和Reddit等共同创造的社交媒体革命。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公司没有一家来自欧洲,因为那里没有这样的保护。
这并不是说美国,甚至硅谷,想到了所有能使创新蓬勃发展的法律工具。例如,美国移民政策,无知地将刚刚完成学业、准备好可以开始创新的工程和商管学生送回母国,即使他们更愿意待在美国从事创新工作。同样适得其反的,是迫使外国收益在境外花掉的税法,而不是让它回流,并在本国投资更多的创新。
欧洲人,或者其他任何人(当然也包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可以从美国的这些错误中学习,在全球数字市场获得竞争优势,所花费的成本,低于建设校园和种子投资。但是,他们首先必须懂得要在网络经济里创造经济价值,法规(或欠缺法规)扮演的重大角色。